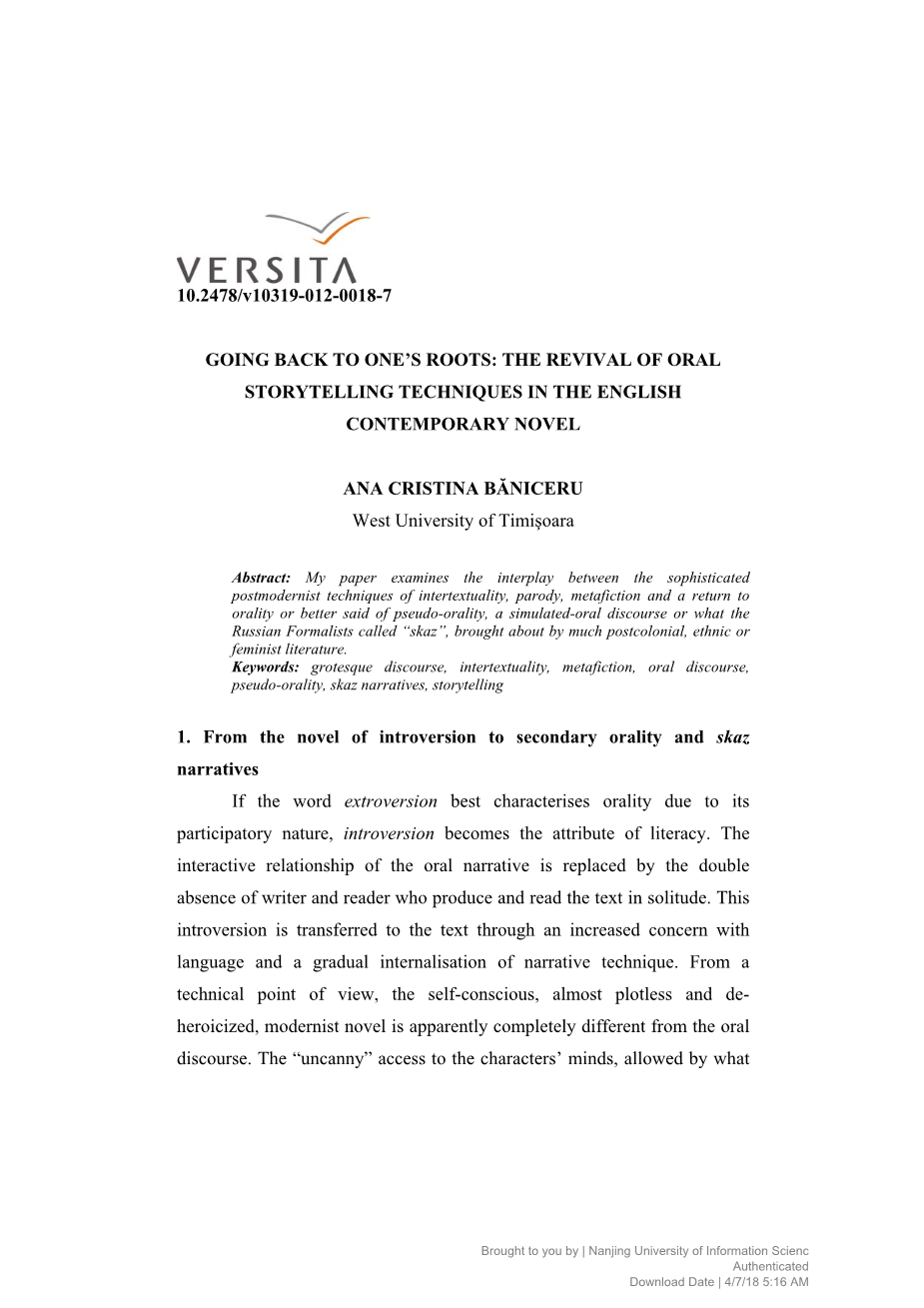

英语原文共 16 页,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回归本源:英国当代小说中口述故事技巧的复兴
ANA CRISTINA BĂNICERU
West University of Timişoara
摘要:本文考察了复杂的后现代主义互文性,戏仿,元小说和回归到口头或更好地说伪口述,模拟口头话语或俄罗斯形式主义者称之为“斯卡兹”的后现代主义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后殖民主义,民族或女权主义文学
关键词:怪诞话语;互文性;元小说;口头话语;伪口述;故事叙事;评书
1、从内向小说到次要口头和故事叙事
如果外向一词因其参与性而表现出语言性,那么内向就成为识字的属性。口头叙事的互动关系被作者和读者的双重缺席所取代,他们在孤独中创作和阅读文本。这种内向是通过对语言的日益关注和叙事技巧的逐渐内化而转移到文本中的。从技术角度看,这部自觉的、几乎没有情节的、非英雄主义的现代主义小说显然与口头话语完全不同。
此外,沃尔特·本雅明在他著名的文章《说书人》(1936)中,悲观地宣布传统叙事方式的消亡,因为当时的现代主义文学充斥着压抑的世界大战精神。不幸的是,本杰明并没有足够的生活来看到口头的复兴,或者更好地说到伪性,一个模拟口语的话语,或者是俄国形式主义者们所说的skaz,被后现代主义作家广泛使用。因此,出现了新的文学形式:魔幻现实主义、民族主义和后殖民文学。“在写作中,对口头表达的模拟,似乎是想要还原这种媒介的实时交流的情况,这种媒介必须以超脱、孤独、隐私和缺乏语境为特征”(Brooks 1987:36)。这里的关键字是模拟,因为我们所拥有的是对口头话语的模拟,一个虚构,一个模拟。
这一新的口头形式是由Ong所提出的,它类似于原始的口头性,在写作之前的口头性,在它的参与性的神秘主义中,它对社会的关注和对当下的专注,甚至在使用公式的时候。然而,正如我上面所说的,这是一种模拟的口头语言,因此,它是一种更加自觉和深思熟虑的,没有文字和文字的功能。“二次口语是非常像,明显不同于初级口语。像初级口语化,二口语产生了强烈的集团意识,听言语形式者为一组,一个真正的观众,就像阅读书写或印刷文本变成个人自己。但二口语产生不可估量的意义组大于初级口语文化的麦克卢汉的“地球村”。而且,在写作之前,口头上的人是集体的,因为没有可行的选择。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学口语,我们组的头脑,自觉地以编程方式。个人认为,作为个人,他或她必须对社会敏感。不同于主要的口头文化的人,他们因为没有机会向内转而向外翻转,我们因为向外转向而向外转向。在一个像静脉,其中原发性口头促进自发性因为分析思考通过写作是不可用的,二次口头促进自发性因为通过分析反思我们已经决定,自然是一件好事。我们精心策划我们的事件,以确保它们是完全自发的。”(Ong 2002:134)
这是媒体的口头禅,其过分的言辞压倒了我们。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我们都被个人故事、自白所包围。每个人都想讲述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需要观众。我们有脱口秀、真人秀、政治辩论、个人博客、站起来的喜剧。我们有一个模拟的回归到原型故事的场景中,一个讲故事的人坐在他/她的观众面前,而这反过来又在表演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关键字变得外向;一个外向的人推到了它的极端,在小说中也被颠倒了。因此,这一典型的讲故事的场景在skaz文学中反复上演。
根据Kenneth Womack(2006: 115)的说法,skaz仍然是俄罗斯形式主义者对文学批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斯卡兹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俄国散文中所固有的一种富有质感的叙事技巧,是根据口头和民间故事的文体要求,以隐喻、主题和观点功能为基础的文学作品。
这个词来自俄国的斯卡兹,意思是“说”和从语义上讲,它与“短篇小说”和“童话”相关联。雅各布·L·梅伊(2000:166)把小说和同质小说联系起来一个人正在向别人讲述他和她的故事,因此这个对话式的是以“寻址性”为特征的。据同一作者说,这个叙述口语语篇与白话语篇有着密切的联系。梅伊(2000:167)也把黄鼬和方言联系起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眼睛”方言或语音偏差:“总体上黄玉的故事体裁被涂上了颜色,白话对人物语言的侵入(包括叙述者作为人物的语言)“。
巴赫金区分了两种类型的黄玉:简单和“模拟”黄玉。前者是由巴赫丁所称的第二种语言(被代表的人的客观化的话语)构成的;这是莱斯科夫的口头叙述的例子,根据巴赫金的说法,他使用skazz不是因为它的口吻,而是主要代表“一种社会的外国话语和一种社会上的异域世界观”(Morson amp; Emerson 1990:153)。后者,以果戈里的“大衣”为例,是由怀疑的斯卡兹或对话的斯卡兹(带有“引号”的意思,它不仅仅是口头语篇,它还显示了对另一个人独特话语的定位)。据莫森和爱默生引用的巴赫金说:据莫森和爱默生援引的巴赫金说:在短篇小说中忽视对别人话语的倾向,因而忽视它的双重声音,就会被剥夺对这些复杂的相互关系的理解,一旦声音变成不同的方向,它们就可能进入话语的范围(1990:154个)。
对弗鲁代尼克(1993:107)来说,斯卡兹是“一种讲故事的方式”。模仿和文体口述“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述中都可以遇到。在后一种情况下,它的形式是共同意见,它可以发展成村民的声音,从而与读者建立一种同情的联系(Fludernik 1996:220-221)。最近的小说经常采用这种叙述方式,其特点是过分的地域性和使用方言或方言。提到萨尔曼·拉什迪的《午夜的孩子》,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脸,安东尼·伯吉斯的《发条橙》,珍妮特·温特森的《激情》,杰弗里·尤金尼德斯的《处女自杀》,就足够了。最近的skaz的例子是高度的对话,用巴赫金的术语来描述另一个人的话语,这就引出了互文性的下一个主题。
2、后现代主义与口头故事叙述技法的复兴
在写作之前,作者的概念并不存在。没有作者,只有故事讲述者或叙述者,因为没有作者,我们不能谈论原创性,也不能说我们的概念。表演本来可以是原创的,但不是故事本身。事实上,他们所做的是回收和重新安排那些在过去被证明是成功的情节或主题,换句话说,他们和他们在一起;根据观众的需要和欲望加以修饰,当然,这在叙事的制作过程中扮演了非常积极的角色。在没有任何重新编码设备的情况下,重复使用变化也是必要的:没有重复,一个故事就会丢失。这是互文性的一个方面:回收旧故事,编织不同的叙事线索。我想不出一个更好的比喻来说明这一点,比拉什迪的《哈罗恩的故事海》更贴切。传统上讲,故事是偷来的,乔叟偷了他的;或者他们被认为是文化或社区的共同财产这些引人注目的事件,无论是想象的还是真实的,都是在一种纯粹发生的情况下,以历史本身的方式呈现出来的。
然而,口头故事缺乏的是故意的讽刺或讽刺性的维度,这是互文性的一个典型特征。如果没有作者的存在,我们就不能谈论作者与叙述者、作者和故事之间的距离,而没有距离,我们就不能谈反讽(反讽意味着距离和作者身份)。当然,我们确实有故事讲述者和人物、听众和人物之间的距离,因此,由于故事讲述者和听众都有共同的立场,他们的描述中产生了幽默。但这是另一回事。而且,如果没有任何记录诸如写作或印刷的方法,就几乎不可能重新访问一个故事,并以一种拙劣的方式重写它。然而,口头传递的故事和互文性之间可能的联系需要仔细的重新考虑。
互文性的问题引出了下一个话题,即图元化或哈钦所谓的自恋叙事(1999:203)。口头传递的故事假定一个讲故事的人在观众面前表演故事。写作的发明导致了故事讲述者和听众的消失,以及作者和读者的出现。但是作者并没有在读者面前写他/她的作品,因此,口头叙述的互动关系被作者和读者的双重缺失所取代(叙述者和叙述者的双重虚构)。在口述传统中,在同一观众的帮助下,在观众面前创造了叙事。通过写作,叙事过程变得不可见;这是许多现实主义文学的例子,它们急于模仿现实,隐藏了文本的脚手架。当小说家揭露文本的隐藏机制,并在幕后吸引读者时,叙事过程就变得清晰可见,因此焦点从“虚构”转向“叙事”,从情节的恰当转向叙事的情节。前者的情节是以行动为导向的,而后者则是以语言为导向的。然而,当作者决定用一个喋喋不休的叙述者和一个活跃的叙述者再现原型故事场景时,就像许多民族、后殖民文学和史学元小说一样,情节本身和叙事情节都成为中心。因此,模拟语言成为后现代主义复杂的元游戏与对情节和故事线的不怀旧回归的完美借口。
更不必说,自恋的叙事,以其超结构的结构,将其虚构的语言系统与读者的观点相结合,将制造的过程转化为阅读的共享乐趣(哈钦1999:203)。根据读者反应理论,读者掌握了文本中意义的关键:当小说家通过文字实现他想象的世界时,读者-从同样的词创造了一个相反的文学宇宙。他的创作和小说家的一样。(哈钦1999:208)
读者在解释一篇文学文本时的这种自由,与作者使用的戏仿、互文性或元理解等新技巧相关联,将作者与文本关系替换为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与口述文学的互动部分平行的,它要求听者积极参与故事的传播和传递。更别提通俗小说的兴起使情节和故事线复活了,无论这两种小说在后现代主义小说中如何被截断。
在关于魔幻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章中,温迪·B·法里斯(1995:164)写到了“补充的”后现代叙述者,以某种方式与“精疲力竭”的现代主义叙述者相反,并称他们为谢拉泽的子女“出生于高现代主义小说的充满死亡的氛围,但有些东西可以超越它”。他们重振了先驱者的封闭话语和他们对可接近性的渴望,我想补充一点,他们回归情节与高度内向的现代主义叙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法里斯(1995:163),谢赫拉扎德体现了高度现代主义的叙述者——“被死亡所累和威胁,但仍在创造”。
谢赫拉莎德的孩子是深深植根于口才的故事讲述者,但由于他们属于20世纪,他们的口吻是主次口吻的混合体。根据Hoogestraat(1998:51),Ong对初级和次级口语的区分被认为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它允许那些被排除在主语中心之外的人。殖民语言用另一种话语来再现他们过去的历史。她接着说,王的作品承认主要的口吻是一种想象他人语言和文化的方式,他们的语言由于殖民压迫而被同化或没有生存下来。然而,重新创造原始的口吻可以被看作是乌托邦式的努力,因为根据泰勒一个纯文化的存在,只有在一个民族记录者的书面记录缺席。对他来说,翁吉安的“主要口吻”和德里德的“缺席”几乎是一样的:“土著人的口头声音变成了缺少文本围绕的中心,没有中心文本就不存在“(胡吉斯特拉记1998:53)。这里的关键词是缺席,因此重新想象和重新创造那些困扰官方“文化”和语言的缺席声音变得非常重要。在这一类别中,我们不仅可以包括殖民者的缺失的声音,而且还可以包括妇女或同性恋者、变性人的缺席声音,清单还可以继续包括疯子,罪犯,社会弃儿。因此,在当代文学中,狂欢节或马戏团的形象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作为一种主张差异和多样性的方式。
一个人怎么能发出声音呢?通过将故事讲述者的角色分配给他们,并允许他们在书面的范围内自由地进行口头讨论。因此,我们遇到了第一人称叙述的扩散,展示了各种各样的独特的叙述者;一种寻找观众的声音的复调,一种注入甚至浸透当代文学的声音的复调。矛盾的是,在许多情况下,口头谈话的消遣需要第一人称叙述。我用“矛盾”这个词,因为在古代和中世纪的口述故事中,个人经历的故事非常罕见。故事讲述者不是个人,而是代表社区价值观的社区成员,他们从传统中获得权威。人们后来开始被视为个人,但只是与神性的关系,与上帝(见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只有当宗教被道德所取代时,我们才能谈论个人的崛起(Fludernik 1996:77)。此外,在口述故事情节中,听者是在讲故事的人在场的情况下,而在写作情境中,讲故事的人是缺席的,而使他/她在场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给他/她一个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声音。
席的声音呈现出一种颠覆性的角色,跨越了话语的界限,成为了一种“本体论”。我在这里采用了麦克海尔对认识论主导(现代主义)与本体论(后现代主义)的区别。认识论的我或讲故事的人(这是康拉德的《黑暗之心》里的马洛的例子)是关于知识和知识的极限的,你可以了解自己和其他人。然而,根据麦克海尔(1987:10)所述,许多后现代主义作品都是在处理违反边界的问题。斯卡兹的叙述者违反了世界第一和风格的界限。我说的世界边界是什么意思?在许多情况下,口头话语与一种奇妙的模式结合在一起,在现实的话语中有一种强烈的渗透,从而削弱后者,因此,许多叙事的坚持,都是一种特定于口头模式的神话意识。我现在指的是史学的超小说,它结合了永恒的说书人的神话意识和历史作家的历史意识(温特森, 拉什迪, 阿克罗伊德,巴恩斯等等)。这种二元性将自身转化为一种准密性,巧妙地颠覆了官方过去的所有主流账户。因此,他们通过记忆的过滤器重新讲述过去,这几乎与集体记忆纠缠在一起:一个神话的宝库,梦想。由于缺乏写作,口头文化无法以系统和详细的方式记录过去,这意味着它们不是由历史而是由神话意识主导的。神话意识的采用使斯卡兹叙述者摆脱了时间和现实的束缚。
此外,根据巴尔 (1999:147):记忆也是时间与空间的结合。特别是在前殖民地的故事中,记忆唤起了人们被殖民者从他们的空间中驱逐出去的过去,回溯到那个地方是另一种空间的时代,这是一种对抗殖民影响的方式。
空间与神话和幻想交织在一起;重新创造的空间,以一个不同的,以前为中心的身份,这个回归到一个神话的空间,也反映在通过一个不同的话语,我称之为怪诞的话语。我将在我的论文中解释这个术语。
有时候,这种奇妙的模式会在童话故事中找到表达,尤其是在安吉拉·卡特(《爱之家》的女主角)、艾玛·坦南特(《狂野之夜》)、珍妮特·温特森(《樱桃的性感》)或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新娘的新娘》)的短篇小说中。然而,这是对童话故事的一种拙劣的模仿;事实上,许多女性作家都采用了这种女性化的幻想,它起源于父权制和异性恋的边缘。在同一类别中,人们还可以将科幻小说和叙述者一起添加到另一种现实中,并对叙述者进行叙述,他们可以是同一个社区的成员。斯卡兹叙述者通常被描述为叙述者或故事讲述者,他们与故事的背景有关,通常是他们的家乡或国家(Fludernik 1996274)。你可以在这里加上另一种现实,不管是科幻小说还是奇幻小说:阿特伍德的《女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24930],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课题毕业论文、文献综述、任务书、外文翻译、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


